刑法设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目的是保护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对于金融管理秩序的具体内容,传统观点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因破坏利率统一、影响币值稳定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第二,因削弱国家通过信贷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第三,因使社会闲散资金失控,社会公众的资金安全面临巨大风险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
比如,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立法说明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项目建设与资金的短缺矛盾十分突出,一些单位和个人为筹集资金,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不择手段地把公众手中的钱集中到自己手中,与银行争资金,从而造成大量社会闲散资金失控,不利于国家集中有限的资金用于国家急需的项目,发挥资金的最佳效益。”许多学者也认可这一观点。基于上述对立法目的的认识,有观点对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范围提出了质疑,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金融抑制背景下的立法,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体制也在不断地进行市场化改革,在此背景下为了保护正当合法的民间融资,应适当限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范围。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破坏金融秩序犯罪,按照法益保护的原理,行为人必须将吸收的存款用于信贷目的,即吸收存款后再发放贷(用于货币、资本的经营),才可能对合法的金融机构如银行正常发放贷款这一业务的开展有冲击、有影响,才能危及金融秩序,才应以犯罪论处。如果行为人将非法吸收来的资金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即便资金用途有所改变,也不应当构成本罪。但本书认为,当前金融市场发生明显变化,非法集资对金融市场的危害也已发生明显变化,对银行存贷款业务的冲击较为有限,仅从保护银行存贷款业务来认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犯的法益已经不合时宜。现行金融领域的行政规制和刑法规制措施,均是建立在传统金融业风险基础之上。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间接金融领域中的信用风险,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直接金融领域中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决定了对金融市场事前准入、事中监管、事后惩治的监管体系的建构。国家对商业银行规定了严格的准入条件和一系列严格事中监管的规则,我国加入的《巴塞尔协议》和《巴塞尔协议Ⅱ》都是监管商业银行风险制定的国际规则。严格的准入和监管规则的最终目的就是保护存款安全,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接受金融监管部门的任何监管,却实施了与商业银行同样的存款业务,其风险不言而喻,吸收资金的规模越大,风险也就越大。而且,随着涉及人员、区域、资金的不断放大,金融领域的风险还会传导至社会领域,影响社会稳定。这些风险的产生,并不源自资金的用途,而来自吸收资金的方式以及其不受任何监管所造成的潜在风险。因此,不论吸收的资金用于何处、都已经产生了潜在的风险,破坏了金融秩序,应当予以取缔,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以避免风险不断扩张蔓延。
从防范金融风险的立法目的出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金融创新也必须接受严格监管。在互联网金融发展之初,一些金融领域专家认为应当对互联网金融创新中的问题给予宽容,不能因为出现问题就将其扼杀在襁裸之中。对此,一些法学领域的专家也表示认同,认为如果刑法过度介人金融领域,频繁地通过刑法手段对互联网金融进行规制,会阻滞和扼杀金融创新,对于那些因经营正当的互联网业务活动而不得已或不小心触及刑事法网的行为,应予以适当程度的宽有。同时还建议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犯罪采用与一一般金融犯罪不同的追诉和量刑标准,以体现国家对金融创新的认同和鼓励,避免将“试错”的刑事责任风险让社会个体来承担,不然会反向冲击刑事责任机制本身的正当性。这些观点没有准确地认识到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相关条文保护的法益。互联网金融或金融科技的理想状态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现代通讯技术等手段来更加准确地评价风险、缓和风险。“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然是金融”,一批研究互联网金融的金融专家都指出,当下互联网金融仍然面临信用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的风险,与传统金融无本质差异。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17年《纪要》)指出:“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然是金融,其潜在的风险与传统金融没有区别,甚至还可能因互联网的作用而被放大……对各种类型互联网金融活动,要深入剖析行为实质并据此判断其性质,从而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打击与保护的界限,不能机械地被所谓‘互联网金融创新’表象所迷惑。”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始终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当前涉互联网金融非法集资等一系列重大非法集资案件表现出对金融安全、社会稳定的破坏性,这些金融活动并不一定冲击贷款程序,但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惩治仍然是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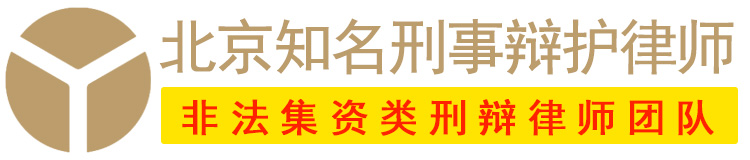

 18801091688(微信)
18801091688(微信)